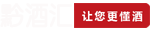在我家,從我記事起,廚房門外靠墻的角落里就有一個被木椅擋住的柜子。我對里面的東西極其好奇,那個柜子逢年過節總是被家里的大人打開。
一天晚上,當大人們都在睡覺的時候,我躡手躡腳地走過去一探究竟。然而,那把實心椅子太重了,我抬不起來,所以它在石頭地板上發出很大的聲音。我也嚇了一跳,大人們都醒了,我慌慌張張逃回房間。
所以只能等春節了。我出生在一個老人眾多的家庭,由爺爺奶奶撫養長大。我家前幾代長輩都生得早,所以那時候全家人都聚在我曾爺爺奶奶家,做了兩桌菜,擺了兩桌酒。我年紀小,喜歡熱鬧,弟弟還沒出生。我是家里最小的,親戚們總是要和我開玩笑,所以過年對我來說是一年中的大日子。所以當時我就蹲到了角落里能看到柜子的地方。一眼望去,只見隱約閃爍著或光滑或多邊形的瓶瓶罐罐,大人們用手捧出一個。
這是什么?'
這是――葡萄酒。白酒。或者最好的白葡萄酒。'

自然不知道白酒是什么,更不知道楷書藝術字連在一起的三筆中間的字。但是瓶子的玻璃邊在燈光下閃閃發光,薄薄的瓶子上貼著紅色的標簽,好像是什么寶貝。于是我看著它藏在我的手提袋里,放在餐桌中央,像這個家的貴客一樣隆重。
除夕夜,午飯前,有一個簡化的祭祖儀式。我看著曾祖父走過去,把那瓶珍貴的液體依次倒到每個座位上。和平時喝水的杯子相比,杯子小得驚人。之后從他開始,我們做了三張“空桌子”。我說完,曾祖父慢悠悠地說:‘老人家的桌子吃完了。’然后我們走向餐桌。但是一張桌子放不下。我和同齡的孩子、年輕的阿姨和叔叔坐在一張小桌子上,而最有價值的長輩,我的曾祖父母、我祖父的三個兄弟,然后是我父親的人,坐在大廳里。我要祝酒了,盡管我一直在喝白開水。一個接一個,我習慣一邊打電話說祝福,一邊瞟著他們小杯子里的晶瑩液體。味道很好,但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只喝這么少。

年復一年,直到我不再是個孩子,我的曾祖父去世。曾祖父第一次不在的飯局上,我坐在大桌前,看著每年放在桌子中間的那瓶五糧液。突然發現,隨著我的成長,印象中的那瓶五糧液,已經不再是一個拿在手中拿不住的龐然大物了。一切真的突然變了。
還得敬酒,還不能喝。每次走完,我只記得每個喝了那一小杯酒的人,喝完之后都皺起眉頭,發出一聲嘆息般的呼吸。我回到我的座位,只聽到我的曾祖母和祖母在我周圍漫步:
男人,老了就是老了.不像酒。英,去和他們喝一杯。'
奶奶年輕時聰明能干,五六十歲了還很健康。她喝了兩杯葡萄酒,容光煥發。她還聽到三紅蓮說,‘嫂子海量’;一桌人趕緊互相舉杯,都笑著互相祝福;兩鬢斑白的曾祖母看著他們,眼睛卻微微泛紅。那天是不同的。中午過后,各家各戶陸續離開。晚上沒有全家人的年夜飯,第二天也沒有團聚。我對由酒引起的過年的期待早已成為習慣,但第二天在潦草的午餐上,我對過年感到失望。也是因為你家里沒有那種酒。是好酒,四世同堂桌上大餐,談笑不斷的時候才能喝。
那是我最后一次坐在我曾祖父母家的大餐桌旁過春節。香香的VIP就這樣被困在了房間的角落里,成了我在繁忙的學業和生活瑣事中慢慢淡去的一個念頭。
當文字和書籍堆積在桌邊,我卻靠著離我一千多年的詩活著。我從杜麗開始,熟悉了白居易、杜牧和高適。我發現唐朝的人總是談論喝酒。看十首詩,至少能遇到兩首談酒。不管送別還是送死,有錢還是沒錢,唐人總喜歡喊喝一杯。李白要當掉值錢的酒,要用余的錢換酒,杜甫沒錢要賒酒.這讓我再次對葡萄酒產生了好奇,我已經失去了最初對葡萄酒的好奇。
于是,漢魏時期的人就狂喝。幾乎所有的名人都酗酒,他們都大喊要喝醉。堪稱古今第一醉的劉玲,竟然大喊‘醉了就埋了我’,看得我目瞪口呆。不過,這倒不如打廣告,聲稱喝醉后:‘不小心,很好玩。然而,醉了,醒了;‘聽驚雷之聲,視泰山之形而不見,不感寒熱之肌,色欲之情。’
當然,我不敢喝醉,但又忍不住想嘗嘗酒是什么味道。想到家里存放的上好五糧液,不妨嘗一嘗。

我躡手躡腳地搬椅子,然后悄悄打開柜子,摸到瓶頸細長、邊緣有雕花的五糧液,摸索著找瓶蓋。可以扭曲。挺好的。所以我把它拿出來,翻找我以前見過的任何小杯子。晚上不敢開燈,只好用手摸,差點讓一個杯子從柜子里掉出來。還好有驚無險,但還是被查出來了。
借著一點月光,我在廚房拿著瓶子倒了出來。我的呼吸充滿了熟悉的酒香。我盯著桌子上晶瑩剔透的液體。薄薄的微光有一種說不出的美,讓我盯著它看了好久才反應過來。未經授權,請將此人請出。
的貴賓送回去。我想著這是那些千古聞名如星辰的人念念不忘的飲品,腦子里閃過"勸君更盡一杯酒,西出陽關無故人"、"晚來天欲雪,能飲一杯無"、"塵世難逢開口笑,菊花須插滿頭歸",慎重地舉杯入口,讓酒液在口中打轉;辛辣從舌過喉再落肚,一時滿腦子只有驚異,怎么想這也仿佛不是一個如夢似幻的味道啊;然而濃香馥郁,直到我心有戚戚地入睡。
曾祖母去世是去年的事。她去世之前,我們雖沒能回昔日的大屋中過年,但也去她所住的三公家的附近或是別的餐館,吃過幾頓圍坐一桌的飯。我最后的印象是她在去年年初時拉著我,口齒含糊地問長問短,早已不再是當年能夠為整個家族做兩桌大菜、手藝獨絕的人。然而她記憶中,我還是那個最喜歡喝她特地給我做的酸奶的、那個最小的孩子,而不是我已經上了小學的幼弟。
今年過年時,三兄弟的三家人還是坐到了一起。我看著每個人連同我面前的小酒杯,我已經完全能懂為什么這杯子這么小了,我成年了。
"媽走了,"我聽見照顧她最多的三公說,"就剩我們兄弟幾個,以后大家相互照應,不要讓她老人家在天上寒心。來,我先敬你們。"
一輪飲過以后,是我的祖父,三兄弟的大哥;再是我的二公,三兄弟的二哥。他們一輪輪地喝,一圈圈的敬,兄弟之間又一杯接著一杯,邊敘邊飲,直到大醉酩酊,從相互供著家人生活掙工分開始說起;姑婆嬸嫂說著囑咐的話,一桌子觥籌交錯,已經擺了十多年的五糧液再做了一次客;它居于玻璃桌上,仿佛一直在看著。它看著一代人兒孫滿堂,看著這代人逝去,又看著下一代人,最終也看著我。
盡觴之后,云開雨霽,各家須尋各自門,一代賓客亦退席,喝過了、送過了,便理應振作精神,醫生該坐診切病、老師要教書育人。那晚,這瓶最后剩下一瓶底的五糧液就立在桌上,身邊是盛著前一天剩飯的白瓷盤,面前是一個人靜悄悄地來看望的我。
我把它一手托了起來,拿到窗下。酒瓶棱邊凸而不銳,玻璃在月下光澤流轉,我摸到正面玻璃棱邊整齊地消失的地方,金色與紅色若隱若現,說著它身份貴重,一如從前。哦,本該如此,酒不像人;老了也不褪其色,不改其質,好酒更是如此。
一人飲下這樣一杯酒,恰似用亙古來解須臾。酒液凜凜如刀的風味入喉,淳淳如醴的香氣入心,能縱人痛快,也能平人不平。再大的事,一仰脖的一瞬,總是能一口喝盡,化作一口蕩氣回腸的酒香隨風而逝。

"勸君今夜須沉醉,尊前莫話明朝事。珍重主人心,酒深情亦深。
須愁春漏短,莫訴金杯滿。遇酒且呵呵,人生能幾何。"
酒不同任何飲品。
酒同金玉。
再也沒有什么液體能承載比它更深的愁、更長的憾、更重的情。